中国画,向何处去?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一直被当作一个重要课题。这个课题,既不能单独依照理论家的主观臆断和逻辑推理,也不能完全凭借实践家的创作予以完美的解答,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重作用下寻求答案。其方向是由它的内在精神、基本特性、现实语境和价值取向决定的。
中国画的基本特性和内在精神是此问题的逻辑起点。20世纪初西风东渐,有了西方文化作参照,中国画的特点就更为凸显。不像西画受科学和宗教的影响,中国画深受哲学和文学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成中英先生有着极精辟的概括: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性的自然主义,以及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具有某种特征同构性。前者对于后者的作用则体现在:以人为本,以自然之生命样态为依托和凭借,以完善自我并和谐于天为终极关怀。在此基本框架下显现中国画特有的样态和性情——类型化与范式化——此为中国画从生成、样态、方法、机制到精神诉求和终极关怀各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借此方式获得某种共识和约束以及情感交流和释放,并具备审美与教化的双重功用。与类型化相对应的是 “意象”的思维方式与“写意”的造型观。对于画家而言,类型化既便于进入相对保险和便利的状态来释放和疏导情绪,保证艺术品格,又使绘画思想和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类型化与传统中国画的功能与意义有直接关联,它的内在省察与陶养性情之功用大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表现。与文学和书法的联姻以及由此确立的价值标准即是最好的佐证。它使画家离开客观限定而进入主观营构,由形而下的描摹进入形而上的精神体验。这也是中国画家所津津乐道、一往情深之处。从另一面看,则限制了艺术新经验的生成,限制了中国画革命性的演进。因为这一层原因,中国画演进方式常常是托古改制、返本开新。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画之变革相对比较中庸或折中。究其实质,是为完成秩序的架构和情操的引导,从回照自然、远离尘嚣中提升人格意义的雅致高蹈,在平淡天真的极境求索中臻于儒之敦厚、道之清虚和释之超凡。由观瞻到思考,在墨戏书写中确立创作者和欣赏者之精神世界的充实、愉快和自足。这是传统中国画(主要指文人画)的大部分意义所在。这种高妙,一旦被无数次复制,脱离了具体的、真实的情感,脱离了社会现实语境,则渐次演绎为空洞无物、聊无生命的样式,也便宣告了其生命力的终结。
20世纪初中国画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人们对中国画脱离具体情感和社会现实的质疑终于演变为一场“美术革命”,这无疑是针对文人画之弊所作的纠正,虽然发起者多是康有为、陈独秀等圈外人,亦不免偏颇和激进,却使中国画步入现代转型之路。一百年间,有三个大的节点应该予以充分的关注,它们是:20世纪初的“美术革命”、 20世纪50、60年代的“新中国画”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85新潮美术,这三次革新一步步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画样态,我们今天谈论此问题亦是循着这个脉络推进的。在全球化特征凸显、社会形态转型、生活方式多样、节奏变化加速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当代艺术语境有着多元化、个性化、简化、平面化、时尚化、大众化等特点——这些也将构成影响中国画路向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对于传统和当下语境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变革中国画的思路和方法。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画的变革从根本上是强化艺术与社会之关系,重新确立艺术反映社会现实的功用。上述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取得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讨论中国画取向的必要依据。由此我们明了了中国画的去向:中国画必须在历史文脉演进链条上融入时代新意,寻求与当代文化语境相匹配的样态,这是社会文化现实对中国画的要求,也是艺术生命存在之显现,更是中国画向何处去的方针所在。
中西融合,是20世纪中国画变革最主要的方式和特点。凡事一经开始,便有三生万物的效应。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价值判断正逐渐走出文人画一统天下的单一境况。20世纪50、60年代,主题先行,以深入生活式的写生为契机,强调推陈出新,提倡以“新中国画”反映社会现实。85新潮美术对西方艺术的引入和吸收更为全面和多样,其着力点也是对传统美学观念的突破以及对笔墨语言的广度拓展,张扬语言本体意识,虽然这一阶段艺术呈现出对前期单一模式进行反拨所特有的张力,却仍缺少深层的形式转化,但经此洗礼,画家们更加重视中国画与其所处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潮的对应与表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对民族传统和中西融合的方式和方向进行反思,对艺术形式予以探索,为当代中国画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切实依据。
中国画向何处去,在操作层面遇到的最大、最具体的问题是笔墨。在很多人心中,言中国画必谈笔墨。笔墨的有无、优劣是作品评判的标准和茶余饭后的话题。言笔墨必然想到笔墨程式,以至于把笔墨程式等同于传统。事实是,前者演绎笔墨自身的美妙与完满,使画面耐看和好玩味,是个变量;后者常与僵化的表达和空洞的躯壳为伴,是个不变量。不容否认,笔墨关乎中国画的观物、观看方式。观物,中国画以物为中介,笔墨这种语言弱于写实,易于抽取与概括,适合中国画的精神要求。观看,中国画于养性修身功用颇大,笔墨解决了中国画作为视觉艺术原本缺乏的“可看性”的问题。笔墨既是画家抒情达意和状物造型的手段,同时笔墨的可玩味性真正成了中国画的一个看点(在笔墨特有的启承转合和提按顿挫中进行观看)。失去笔墨,必然使中国画的观看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可读性,由看而思,由思而对人生和社会有所感悟,透过对笔墨格调、品质的赏析和评判,引导观看者进行潜在与隐性的道德性揣度,而笔墨品格与人格之间的联系是其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这种深藏于内的导向性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而这种方式比起那些直白浅显的宣传来得更为深刻和内在。民族凝聚力,隐性原则——笔墨含蕴了中国传统特有的道德法则的内化与超越,暗含着道德法则与主体行为统一与融通的内在规定,南宋朱熹说得好:“有道心则人心为所节制”,这便是其中的文化力量。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既然由看而思,由思而知,也便规定了知的范围和深度,有可能限制更大的认知,同时,因为文人画的欣赏群体是文人士大夫,是少数人群,在飞速变化的当代社会,其受众的扩大以及展览空间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的局限自不待言,中国画之革新从此处亦有考量。跳出笔墨之争,站在世界角度加以审视,笔墨也是中国画被世界认可的阻力所在。从接受来看,意境往往比笔墨更容易解读,意境并没有构成欣赏者的障蔽。因为笔墨是艺术家确立自我、推陈出新所面临的具体而微的问题,近世中国画变革便从消解传统笔墨开始,这一点,在林(风眠)、吴(冠中)体系中表现尤为突出,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来谈,其功过得失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明了。
窃以为,中国画不应是博物馆艺术,而应确立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形态。中国社会之变,从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审美取向,都应该渗透到中国画变革的方方面面,使中国画具备反映时代的风向标。这不等于说要求中国画舍其独立性,恰恰相反,没有时代创造性的艺术是绝无独立可言的。行家看得出,没有对应时代的样态,艺术之社会功能也将大打折扣。形式是隐蔽和秘密的,其实作用更大。以文化推动社会的进步,如何推动?艺术家应做的工作是,把艺术本体语言推进和现实表现有机统一起来。在此过程中,坚持主体原则和本体意识是根本,即把挖掘传统中国画中的现代因素的可能性放在首位,确保民族特性延续。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画更加注重将西方艺术经验纳入中国画特有框架中进行转化,中西融合步步深化。不少画家已经意识到,以形式语言转化为核心,而非只停留在题材内容的转换。有效借鉴、消化传统与西方等多种资源,秉持多元、开放精神,大胆借鉴当代视觉经验(如影像等),以此探索中国画向前推进的多种可能性。
中国画向何处去?答案确乎在20世纪中国画的各种理论交锋和创作实践中逐渐显现。今天,笔墨方式的多样化与多元化正日益被认同,人们不再斤斤于笔墨,而是把中国画更本质更核心的精神传递作为第一要务——这恰是多元文化景观最好的表征。向何处去,没有唯一和不变的答案,最好的答案蕴含在不断的探索和变革中。我们的探索方向是:它既能承继中国画的传统精义,又能反映当代社会语境,既能连接过去,也能开创未来。怀抱这样的理想,我们出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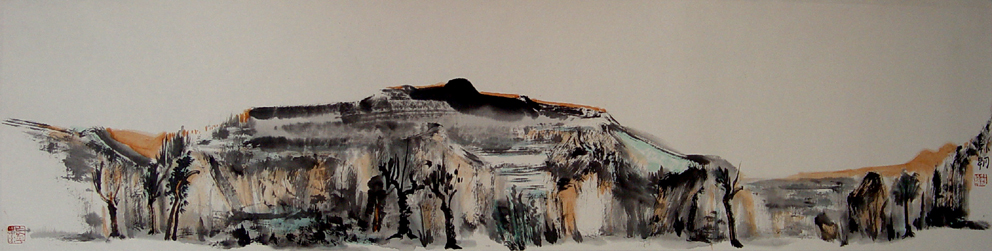






发表评论 评论 (0 个评论)